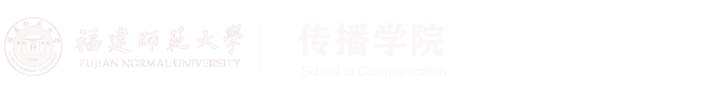2018年4月16日上午,赣江青年学者、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陈世华教授为我院研究生带了一场题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与理论逻辑”的精彩讲座,我院教师黄华副教授、吴鼎铭副教授、林颖博士等人参加了讲座,吴鼎铭副教授与陈世华教授就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关议题展开学术对话。讲座和学术对话由张梅教授主持,我院近百名研究生聆听了讲座和学术对话。

陈世华教授从他绘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三代学者谱系图入手,分析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依照这个谱系图,陈教授系统讲解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基本路径及其演变、学科反思和修正以及给中国传媒带来的启示等。在这个谱系图上,达拉斯·斯麦兹和赫伯特·席勒居于第一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核心位置,乔治·格伯纳和诺姆·乔姆斯基则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另两个起点。陈世华教授认为,斯麦兹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奠定基础;席勒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精神领袖,他以更具有激情的理论创造,扩大了该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通过讲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分支,陈世华教授进一步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陈世华教授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涉及电影政治经济学、新闻政治经济学、互联网政治经济学、信息政治经济学和广告政治经济学等几个重要分支。谈到电影工业,陈世华教授认为,它的扩展具有政治经济内涵,它实际上是推行美国式的价值观念,欧洲电影工业依附于美国电影工业,同质性在增加,本土文化在逐步消失。而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另外,他强调信息的本质和功能是信息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工具,信息无处不在,重现了福柯的全景监狱的特征。对于教育商业化,他认为互联网对教育产生冲击,人们把教育权力让位给经济权力,教育的自主权力在下降。最后谈到自由的幻象,他提出互联网不会带我们进入自由的乌托邦,尤其是大数据时代,只会让我们无所遁逃,所以奥威尔所说的1984会重新到来。
陈世华也对该学科做了反思:“我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可以归纳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整个传播流程都是不自由的。首先是不自由的政策制定过程,媒介是不自由的,包括复合体、新闻管理、媒介垄断、宣传模式、媒介依附都是为了证明传播的不自由,传播过程是不自由的,都是受制于美国核心权力。受众是不自由的,如受众商品论、思想管理、全景分类等。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相比是比较乐观的,有自由传播的期待,认为未来是可以改变的,而文化研究是看透世界后的无奈。”
谈到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中国传媒的启示时,陈世华说:“中国学者要找到自己的主体性,不要被西方牵着走,传播学者承担道德责任,寻求和告知真相,这是最基本的公共伦理。还要保持独立的姿态和左翼的批判取向,不要依附于任何现实力量。也要做到批判与建言并行,应该又破又立。另外,要超越学术的参与,学术研究不能只在象牙塔里进行,应该参与到实践中去,最后就是清晰浅显的教学和表达方式。”
最后陈世华讨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在何方的问题,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社会,首要的任务是回溯马克思,挖掘马克思的生命力。其次也要重视研究对象转移和研究视角下移。他认为传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视宏观理论,不重视社会实践,应该从传统制度转为个体关怀,避免论证乏力、空喊口号。在学科边界上,陈世华认为文化研究与批判研究既有融合又面临着冲突。
作为我院学术活动的一种形式创新,陈世华教授在这次讲座之后,与我院教师吴鼎铭副教授就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旨趣与发展方向进行了一场学术对话。对话一开始,吴鼎铭提出了自己对学术理论的看法:”我更倾向于把学术理论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从格伯纳的‘涵养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是可以打通的,给我们提供一个视角,即在研究的时候沿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声音,从而形成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
陈世华认为中国和西方都需要学派,没有学术社群很难形成一种范式,没有范式难以转型。对于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能否合作,陈教授认为有合作的趋势,他们可以在一起共事,但强扭的瓜不甜,批判学者和主流学者的合作并不融洽,如格伯纳和斯麦兹。
吴鼎铭关于“不自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不自由的传播’是统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念,但批判之后要走向哪里,我们只有理解了“自由”才能更好界定“不自由”,所以当我们强调不自由的时候,什么样的媒体或行为叫自由?”陈老师认为左派作为领导人、公开的政策讨论、公共控制这些都是走向自由的途径,但这些都难以实现,。
吴鼎铭又提出西方思想和中国具体的关系问题:“今天互联网时代如果仍然沿用马克思的术语和逻辑来研究问题,是否会陷入到一种所谓的用西方思想解决中国问题的逻辑中,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如何超越这种逻辑?”对此陈世华给出自己的解答:“现在关于信息社会有两种认知,一种是信息社会是对传统社会的颠覆,一种是对传统社会的延续,看每位学者自身站在什么立场上。我认为互联网时代并没有超越传统媒体的框架,互联网仍掌握在巨头手中,是换汤不换药的形式,互联网没有让我们更自由。”
吴鼎铭也对陈世华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说道:“这本书的导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你最初进入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个领域,是认为当下的学界对于这个领域存在误解和偏见,所以我们花了这么多年时间对这个理论进行梳理,可是到最后发现好像这种偏见和误解挺合理的。”
吴鼎铭针对学界提出的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过于宏大,缺乏微观问题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以自己今年发表在《现代传播》上的论文《作为劳动的传播:网络视频众包生产与传播的实证研究——以“PPS爱频道”为例》为案例,提出应该观察到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说:“社会上存在一些谬论,认为网络视频的生产与传播代表了公民的权利,可以改变中国生态甚至推进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发展,但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在他们拍摄、制作、上传视频的过程中,其目的只是为了吸引点击率,获得广告收成,从这个角度分析,受众是一种商品,他们的传播力被转化为了一种劳动力,我们用实证研究方法佐证了传政中关于剥削、资本的结论,所以沿着这个路径,把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运用到中国具体的微观问题之中,能纠正一些文化研究的主观想象,从而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对于传播学中国化的问题,陈世华认为我们不需要把传播学中国化,但我们需要在传播学中加入中国视角、中国智慧。而黄华老师基于个人专著《语言革命的社会指向》,以自己的论文《从“天下”到“国家”:清末语言运动中的“声音”和言语文化》为例,谈到:“本土化还是要从中国本土的问题去研究,学生做论文会倾向于理论先行,但我觉得要先有经验性材料,否则就只是用事实去证明西方理论是否正确。我的初衷就是研究为什么中国的文言文会被白话文取代,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想从传播学、文献学角度切入去讨论这个问题。”
(供稿 薛凯丽)